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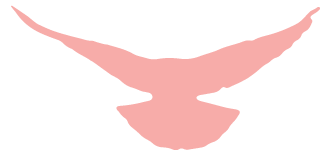


泰和
红色记忆
泰和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,有着深厚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资源,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著名的原中央苏区县。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,泰和的革命先烈们革命理想高于天、革命信念坚如铁,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、为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,谱写了一首首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泰和壮歌,镌刻出一部部可歌可泣、催人奋进的泰和篇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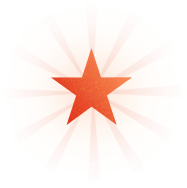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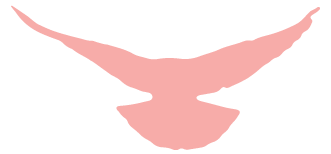

党史专题篇
“三亲”人员对马家洲集中营的回忆(之二)
——马家洲集中营经历记
我,刘显,1938 年上半年参加湘赣边区安福县委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时,曾化名刘大道,现年66 岁(1918年出生),江西省安福县江南公社上里大队油革塘村人。
1940年农历9月,我在十里保学教书时,国民党安福县政府的特种科员(中统特务)刘任文打电话给一区公所通知我到县去填一份教师登记表,以此为名将我关在安福监狱。1941年农历6、7月间,把我解往吉安监狱关了十天左右,便转解泰和县。首先在泰和县国民党调统室执行所住了一晚,第二天押往国民党保安处驻地俩塘村,在里面关了一个星期。由马家洲集中营(对外叫青年留训所)派了两名省警总队的警察将我押到集中营去,直到 1944 年农历7月底将我释放回家。我被捕是由于原莲花县委书记朱许生被捕后为敌效劳,充当特务,把我供出来的。嗣后将我送进安福监狱审讯我的也是他。我被捕时公开身份保学教员,实际那里我担任了地下党的青年干事。
马家洲集中营地点在离马家洲约五华里的松山村,共占用了四幢房子,其中一幢祠堂,三幢民房。这四幢房子平排并列,里面用竹篱围了一层,竹篱笆外面用砖和石头砌了一道围墙,内外两层,戒备森严。竹篱笆里面有看守人员巡视,围墙里面有警察守哨。祠堂是囚禁男人的地方,关着敌人认为问题不太重要或已搞清了的。祠堂隔壁第一道民房是关敌人的重要政治犯,如廖承志、漆裕元、张文彬、吴建业以及初进集中营敌人认为问题严重没有搞清的人,而这幢房子前面一幢是他们办公的地方。据关在集中营的人讲和 1943 年上半年开始安排我在里面弄饭,得知马家洲集中营平时关押的政治犯一百一、二十人左右,最多达到一百五、六十人。后来,抗日紧张、日寇接近泰和时也关了七、八十人。
从表面看,敌人在马家洲集中营有这些管理和看守人员:所长一人(因其外称为青年留训所);训育员三、四人,负责主持审讯、找人谈话、办理案子;管理员四、五人,主要负责管理生活、点名、做操、查号子、参加审讯;服务员(即看守)十多人,其中有两个省警总队分来的女警察专管女号子是穿警察服,其余男看守都着便服。此外,还有会计、出纳、办伙食的事务员等三人。
据我所知,马家洲集中营所关押的人,一是被敌人所破获的共产党员;二是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人士,多半是青年知识分子;三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认为的危险分子。除此以外,还关过一个日本人(究竟是什么身份,我不清楚)。如我党的领导干部有廖承志、漆裕元、唐敬屹、李句良、姚博等,民革成员黄贤度。
敌人对关押的人员采取了许多迫害手段,进了集中营,首先由训育员找谈话,诱骗你讲出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员,担任了什么职务、组织和人员情况等,如果不讲,便施以刑罚逼供,诸如:踩扛子、灌辣椒水、冷天绑起扒掉衣服泼冷水、打地雷公、坐飞机(双手双脚反绑悬起来吊打)、坐老虎凳、绑在电话线上摇电话机触电等。不讲,过几天就用一次刑,步步升级,越搞越厉害。各种刑法用尽后仍然不讲的重大政治犯,则整天脚镣手铐关在房子里,等待反动当局特务头目下令后处死。在我没有进集中营以前,特务就杀了两个革命同志,姓名不清,是我被关在集中营以后漆裕元对我讲的。他说,一天夜里把两个被捕的同志叫出号子,后来听到枪声,第二天这两个同志再也没有见过了。另外还有吴建业同志被杀害,我是知道的,大约在 1942年上半年,吴的爱人范季华、妹妹吴文华先后被抓进集中营,不久的一天夜晚,吴建业被叫出号子,只听到不大的两枪响,以后就没有见过吴了。听漆裕元他们说,吴建业同志已被集中营的特务秘密处死了。我是1944年农历7月间出狱的,那时张文彬同志仍然关在马家洲集中营,他是敌人所谓的严重政治犯,单独关在一间房间里,戴着手镣脚铐,什么刑罚都受过了,他经常绝食,以示对敌人的抗议。1945年间,我才听说张已死在集中营,是折磨致死或是枪杀,那我就不清楚。
被关在集中营的人每人每天只有八、九两(十六两制)米吃,都是霉烂变质的糙米,菜多是萝卜、青菜、豆腐、豆芽等一些卖不完的下脚菜,菜少汤多,又没有什么油。关在里面不见太阳,身体都被拖得瘦弱不堪。许多人经常患病,得肺病的多,反动政府规定“犯人”的经费开支,多被集中营的大小特务、管理人员贪污了,所以伙食搞得非常坏。
在集中营,每天早晨会上操,所谓严重政治犯一天关到晚不让出来。每个星期一要做纪念周,听所长和训育员的讲话,对我们作反动宣传。不外是说三民主义怎么好,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,美帝怎么强大,八路军在延安怎么坏等等。平日上午、下午组织被关人员学习,内容有《三民主义》、《总理遗教》、《中国之命运》以及托派、特务叶青所写的咒骂共产党的反动文章。有阅读能力的组织自学,文化低的听训育员等人讲课,里面还办了墙报,是种不定期的刊物,由关在大祠堂里的一般政治犯或问题供得好的人写稿,都是些适应特务需要的所谓拥护三民主义、拥护国民党、反对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心得文章,许多人都迫不得已写了这些应付文章。但是,他们所谓的严重政治犯是不会叫写,同时也是叫不到的。除了每星期会组织两次学习讨论外,逢国民党的什么节日也会组织一些所谓的座谈讨论,目的是强迫大家改变观点,接受反动思想的灌输,从而瓦解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斗志,就是集中营里借给大家阅读的大量反动书刊,也都是围绕这个目的。经过关押一段时间,集中营的所长、训育人员认为学习成绩好,表现不错的 (他们需要材料都到手了的)可以保释出狱,具保的需要两个国民党员担保。
敌人为了破坏国统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,使尽各种阴险手段,硬的不行,来软的,直路不通,走弯路。比如:利用叛徒充当训育员,以其了解共产党较多的情况,主持审讯,搞攻心战,进行反动说教,实行政治诱骗,原中正大学一名地下党员王重实,抓来集中营以后叛变了,释放后马上留在里面当训育员,还有郭萌辉也是这样,这就叫用“共产党〞打共产党。另一种办法是,把特务装成政治犯,混在被捕者当中,诱骗被关在里面的难友吐出真情,收集材料,向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告密。当时被关在里面的一个大学生杨锡瑞,曾被混在难友当中的一名特务所告密。
绝食抗争
尽管敌人使尽各种办法迫害关在集中营的政治犯,但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、进步人士,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,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,在集中营虽然我不清楚,同志在表面上也看不出有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存在,但是除去少数坏蛋外,大多数的难友默不作声地在狱中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,和敌人进行斗争。在我关进集中营以后,曾听姚博等人对我讲过,我没关进去以前,为了反对敌人贪污伙食费、改善被关人的生活,当特务头子冯琦来视察集中营时,都有向他揭露所里贪污的事实,当面责问,要他改善伙食。许多事情我们明搞不赢,就暗地和他斗。关在里面的难友傅和琛,南昌市汉人,当时患了严重的肺结核,经常吐血,一方面我们向所里提出强烈要求,由大家担保要让他到泰和县城去医治,一方面在其他难友当中凑些钱,给他做医药费,敌人为了掩盖他们见不得人的罪恶,终于允许了。廖承志同志是1942 年被抓进马家洲集中营的,关在重禁闭室左边上面的一间房子里。平时是不会让他出来放风的,与关重禁闭室的张文彬从来见不到面。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,敌人慑于他家庭的重要社会地位,表面上不敢对他怎么样,甚至故意搞些特殊待遇。如让他与张文彬、涂振农 (后在集中营叛变了)吃与集中营职员的同等伙食,在房间里让他看书,允许他画画,唱外语歌也不阻止他。可是廖根本不把所里的大小特务放在眼里,在集中营时,听漆裕元对我讲过:一次冯琦和国民党部一个什么要员来集中营找廖谈话,说什么只要你今后不活动,不要办什么手续就可以释放,廖拒不出狱,立即对他们说:“我有我的自由,我有我的信仰。”廖在狱中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很爱护、很崇敬,对叛徒非常憎恨。张文彬在狱中受尽各种刑罚,毫不屈服,廖经常要我转送一些菜给张吃,当张绝食时,廖要我口头或通过纸条劝他要吃饭保重身体好作斗争。当叛徒涂振农从所里送来一些东西给廖吃,我问他谁送去的,廖即愤怒地说:“是涂振农这个王八蛋的。”集中营的看守姚宝山,比较开明,同情共产党,他辞职不干回家时,狱中部分难友自愿凑了一些钱,送给他作旅费,暗中有的共产党员告诉他到重庆去找何香凝,以营救廖承志。又如张文彬在狱中被敌人折磨得最厉害,仍然坚强不屈,关心难友,鼓励其他同志坚持斗争。1943 年下半年,张得知我母亲去世了思想痛苦,便用纸条写了一首打油诗安慰我,鼓励我的革命斗志。江苏人杨锡瑞,我初进马家洲集中营时,他放在集中营所办的一个更生农场(靠集中营不远公路旁)劳动,搞农业技术工作,相隔一年以后,杨被调离农场关在重禁闭室那幢房子里,什么原因我不清楚。一次被打进难友的特务所告密,嗣后杨在大便时刚好碰上他,便用擦屁股的纸把屎蒙在那个特务的嘴巴上,事情发生后,所里的看守把杨找去打了他们一顿屁股,回到重禁闭室,乘看守不在之时,杨对着窗口喊叫:“头可断血可流,屁股可以打,志气不可屈······”。
(刘显)
来源:中共泰和县委党史办
关注公众号,弘扬正能量

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
 抖音
抖音
 手机APP
手机APP
 快手
快手